夏宁
在传统认知以及实用主义的视野下,经济史或许是经济学大门类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学科了。经济史名家赖建诚所著的《经济史的趣味》这本书认为,罗伯特·福格尔与道格拉斯·诺斯在1993年以经济史的研究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,这个学科才获得基本的尊严。此前,也有至少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写过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论文,他们的研究均使用过历史数据,这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保罗·萨缪尔森(写过不少经济史与思想史的论述文章)、弗里德里希·冯·哈耶克(其著作有浓厚的历史思维)、米尔顿·弗里德曼(著有《美国货币史:1867—1960》)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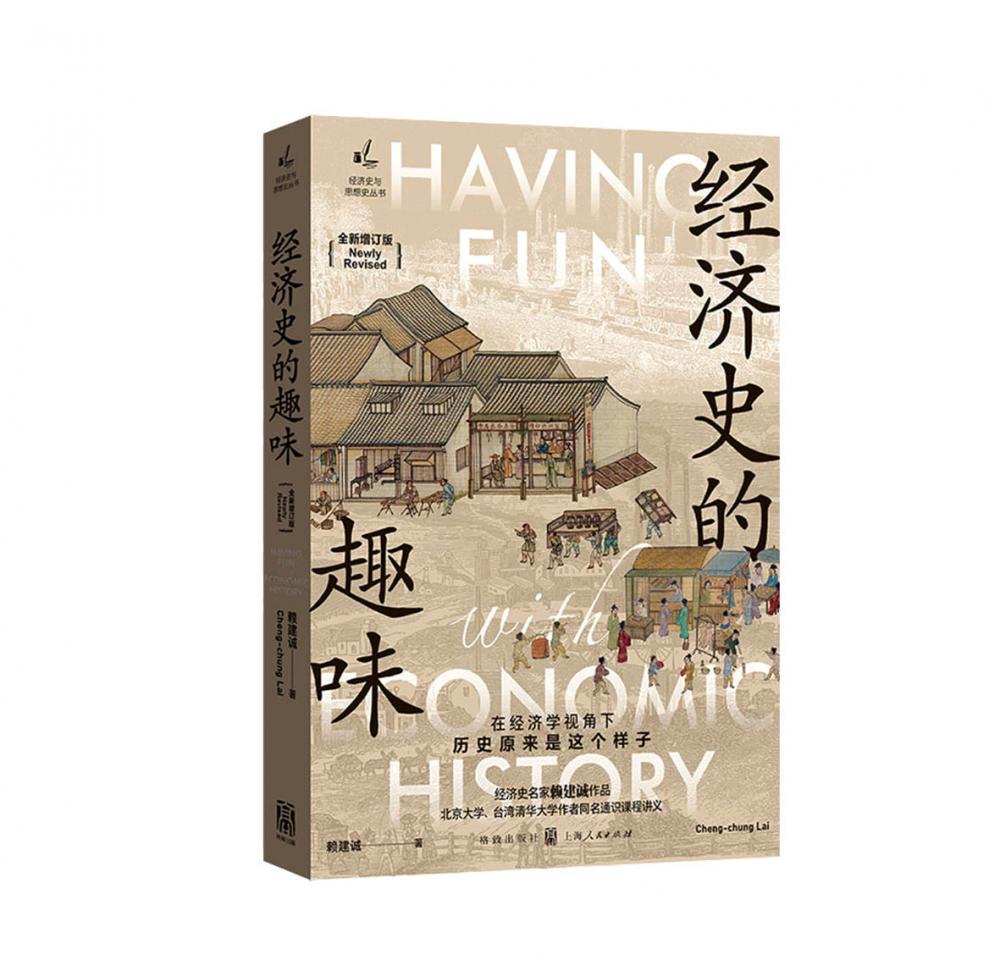
作者强调了经济史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。他认为,如果有效的经济学原理,是根据事实来提炼有用的概念,那么现代的经济学视野,必然受到考察样本的限制。历史能够提供许多当前观察不到的情况,例如研究冰冻层,能帮助理解地球暖化问题。过去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,必然有许多严重的经济景气循环、通胀通缩、货币刚需失调的议题,是今日无法观察到的,也不是现代理论能够解释到的。
那么,既然经济史的研究这么有帮助,为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边缘化呢?作者列举了五大可能的原因:一是,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经济史的人就业困难,但1990年代后这种现象就扭转了。二是,人们误以为经济史研究不如计量经济学那么科学化和定量化,但其实目前的经济史研究已经在大量运用计量的方法。三是,找数据太难。四是,数学能力好的人,更愿意去做逻辑推导的研究,而不是缺乏科学美感的经济史研究。第五,学科比较冷门,缺乏滚雪球效应,不容易出成绩。
可见,作者也很客观,并且他从自身学习研究的经历和感悟出发,同时也综合了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的研究经历,给出了“新手们”实用的建议:如果你的“历史感受”不错,能写简单的数学模型、会统计软件,那么就可以考虑经济史这门学科,会比主流经济学领域更容易立足;而如果你数学建模能力强,比喝开水还容易,能在主流经济学科里出人头地,那不妨把经济史作为第二专业,享受一些历史诠释的视角,说不定有意外收获。
这本书选取了经济史长河中的一些值得研究的事件、经济周期等,为读者展现了一些现象在经济史视角下的独特或是迥异的观点。这些经济事件的挑选,作者遵循了他的“三ing”原则,即interesing(有趣的)、entertaining(有娱乐效果的) 、provoking(有争辩性的)。
首先,我们不妨探究一下:为什么铁轨统一使用143.5cm,且在1937年之后成为了国际标准?原来,最初一些国家(英国、美国和加拿大)和地区修铁路时,均根据自己的技术和传承采用不同的体系,有的地区还故意修得不兼容,以避免其他地区的农工产品进入,类似于一种地方保护主义。此外,各地不同的地形也导致了轨宽差异。最终,美国轨宽占据主流并成为统一标准,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起来后频密的经济往来,促使各铁路公司从利益出发,积极发展跨区兼容的铁道系统。可见,市场需求是规格统一的重要推手。另外,这个典型案例也充分凸显了路径依赖的作用——这种标准轨宽据说并不是最有效率的,但某种历史的偶然导致了路径依赖。此类现象在我们身边的经济生活中多不胜数:为什么不是1月开学而是9月?为什么英国和日本车辆靠左行?等等。
另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例子是众所周知的泰坦尼克号沉船。百年后经济史学者们重新审视了这场海难,而且一并研究了1915年5月17日被鱼雷击沉的卢西塔尼亚号,这艘船被击中后仅18分钟便沉没了,而泰坦尼克号自撞上冰山至沉没耗时2小时40分。经济学家们经过研究得出了结论:若沉没时间比较从容,利他和妇孺优先的行为会出现;若迅速沉没时,就转为各自逃生。而另外两名瑞典经济学家在2012的研究将海难样本扩大到18次,总受难人数超过1.5万人,主要结论也与前述结论类似。所以,作者在书中也感慨到,这与泰坦尼克号电影里种种感人的逃生场景完全不同。
书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事件是工业革命,经济史学家经过研究,“更正”了人们一些固有的经济学认知:早期的蒸汽机和铁路对英美经济帮助不大;传统观念过于强调了英国当时的龙头作用,其实法德当时有些行业比英国更先进;工业革命不只是在英国发生,当时在欧陆诸国与北美同时发展;并不是只在工业革命时期,才有机械化的能力。
并且,作者也据此提出,要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,不只看它的产业成果,社会的发展、教育的普及程度、金融体系的发展、货币制度的流畅化、运输网络的兴建、公共卫生的普及,以及相关制度的合理性,都很重要。
作者称这本书为科普经济史的一本读物。的确,笔者阅读完之后的最大感受是:经济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领域大事件的记录,它还可以提供经济学的分析视角,解释一些现象。并且,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,经常还会面临研究结论有违人们一贯认知的情况。比如书中提及牛顿在1720年南海公司泡沫事件中巨亏2万多英镑一事,此事甚至被一些传记提及,但是相关经济史学家研究后发现并非如此。所以,经济史研究者经常会遇到这种挑战,唯有在研究中秉持客观理性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应对。

